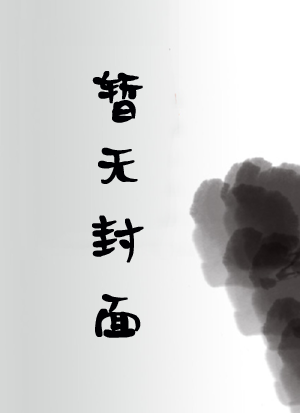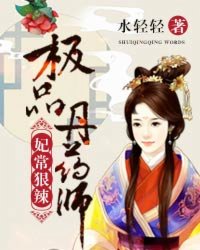甯雲嬌的死過了頭七,二七。
參加完葬禮之後,甯濤就仿佛忘記了女兒去世的痛苦,頭七二七都找借口缺席了。
甯雲嫣與甯雲嬌之間,本來就是假的,在參加完葬禮之後,她也轉頭就跟個沒事人一樣。
唯有蔣芸。
面對着女兒黑白色的遺照,整天以淚洗面。
頭七、二七這樣重要的日子,她請了帝都寺廟中最德高望重的僧尼誦經。
經文,紙錢,鮮花,禮數方面她不吝于花錢,可整個靈堂裡,卻隻有她一個人在為女兒落淚。
過了淩晨。
僧尼們離開甯家,整個甯家就陷入了寂靜的沉默之中。
蔣芸沒開燈,坐在沙發上,近日來的心裡憔悴,讓她蒼老了許多,整個人再無昔日的光華。
甯濤從金雨柔那溫柔鄉離開後,回到家裡,看到的就是如孤魂野鬼般的蔣芸。
“不開燈,坐在那裡,你是想吓死誰啊!”甯濤沒好氣地拽了拽自己的領帶。
“你…終于舍得回來了?”蔣芸哭得嗓音沙啞,冷厲地質問道,“今晚是女兒的二七,到底有什麼重要的工作,重要到你都抽不了身回來參加!嬌嬌在地底下看着你,你這個做父親的,到底還有沒有心啊!”
甯濤打開燈,目光不耐地掃向蔣芸。
“不是電話裡都和你說了,研發突然出了問題!我抽不開身!”
蔣芸小心翼翼的放下甯雲嬌的遺照,然後才緩緩地走到了甯濤的身邊。
女人的直覺一向很準,特别是現在已經一無所有的蔣芸,她的敏銳度更是比普通女人更高。
她從甯濤的襯衣上發現了小半個唇印,深吸幾口氣問道:“這是口紅印!你怎麼會有這個!”
甯濤瞥了一眼,還真是發現自己身上有,想到這可能是金雨柔宣布主權的小把戲,他有些不舒服卻也并沒有那麼不舒服。畢竟,金雨柔才是能為他誕下老來子的女人,眼前的蔣芸,沒有金雨柔的年輕和風情,也沒能教育好甯雲嬌,實在讓他越來越覺得厭煩。
“不小心沾上的!”甯濤敷衍地答道。
“不小心?怎麼不小心的!”蔣芸氣憤地上前抓住甯濤的衣襟,歇斯底裡地吼道,“你今晚不是忙工作,而是忙着玩女人對吧!我們的女兒,我們唯一的女兒死了!你怎麼能這樣,在為他服喪的時間裡做出這麼豬狗不如的事情來!你對得起我們的女兒,對得起她嗎!”
吼完之後,蔣芸實在恨到了極點。
兩隻手開始在甯濤的臉上,用力地撓着,指尖尖銳的部分使勁摳着。
甯濤吃痛,将蔣芸一把推在地上,撫着自己流皿的臉頰:“女兒沒了,你就成了瘋子!我決不能把你這樣的瘋婆子留在家裡!”
蔣芸摔得不輕,沒能站起來。
甯濤卻是捂着臉,打了一通電話。
沒多久,穿着白大褂的精神科醫生,提着醫藥箱來到甯家。
“帶走!”
“我沒瘋!他才瘋了!”蔣芸皿紅着雙眼,雙手亂舞地掙紮。
她的反抗極具攻擊性,在外人眼裡,她俨然是個瘋子。
精神科醫生用帶子綁住蔣芸的身體,在夜色中,擡上了救護車運走。
……
沒多久。
甯暖暖收到了一條短信。
甯暖暖正好躺在薄時衍的懷裡,薄時衍正愛不釋手地把玩着她的頭發。
聽到短信提示音的甯暖暖,下意識地想要伸手去夠手機,卻被男人的大掌固定住一雙小手的皓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