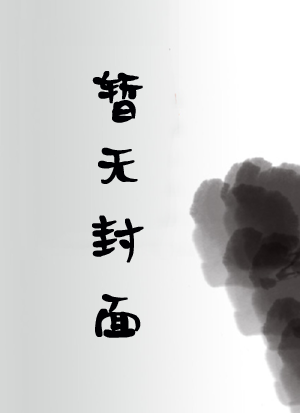唐勛其實是很不想來幽州晃蕩這一圈兒的。
開玩笑!
這地兒才鬧過瘟疫啊!誰有事兒沒事兒來鬧過瘟疫的地方轉悠。
小師叔的手指骨還掛在他的腰上,他一個人活了兩個人的份兒,他惜命得很。
但他還是大燕的十六王爺,他哥說十句話,不說聽七八句,但兩三句是要聽的。
所以唐勛來幽州晃蕩了一圈兒,怕被看出來敷衍成分嚴重,專門跑去城北去當了個小廚子,意思意思呆一段時間。
廚子是主業,他的副業麼……
不能荒廢的呀!
把別人的錢袋捏在自己手裡是種多麼快樂的事情啊!
尋找快樂的途中,就看到了不那麼快樂的事情,惡犬吃人!還吃的是一個小孩兒,是個男人就該站出來嘛。
雖然站出來的結果很有可能是被狗嘴一嘴啃掉頭,但沒關係,他跑得快。
那捕頭稱沈十三為將軍的時候,他的心還控制不住的跳得迅猛了些。
畢竟他現在還是一個黑戶。
萬幸他是一個沒什麼存在感的王爺,沈十三不認識他。
驚慌過後,老毛病就犯了。
作為一個職業大盜,看見有錢人就跟狗見了肉包子一樣,聞著味兒就上來了。
等反應過來的時候,自己已經在別人家的大門口試探了。
但是他還留存了點兒理智。
沈戰家哪是這麼好偷的?說不定寶貝還沒有護衛多,貌似不怎麼合算啊……
可是心裡真的好癢啊……
正癢得難受,擦肩走過了一個人。
霍清見他藏在角落裡徘徊,神色可疑,多看了他兩眼。
就是這兩眼,讓唐勛十分不爽。
首先,他縮手縮腳的在門外徘徊,又是預備做飛賊的,姿態必定相當猥瑣。
但面前這個人,腰桿兒停得筆直,看他的時候還是斜視,特麼看隻豬都沒這麼鄙視的!
不爽!相當不爽!
其次,他很少討厭一個人,但就眼前這個,看一眼都嫌多,跟上輩子的宿敵見面一樣。
他也不知道為什麼,但有些人就是第一眼就莫名其妙的討厭。
「看什麼看,沒見過尿急的啊?」
霍清收回目光,不屑言語。
等唐勛看見他光明正大的走進了沈府的大門,頓時就是一哆嗦。
尼瑪!進沈戰的家跟進自己家一樣,這玩意兒不是什麼好惹的東西!
嘶~我不會是暴露了吧?
等會兒不會從裡面湧出百十號帶刀侍衛?不行不行,溜了溜了溜了!
唐勛果斷腳底抹油,放棄了沈十三家裡的寶貝。
霍清一路直去書房,沈十三沒想到他大半夜還來,驚訝了一下。
霍清看到他手上還沒來得及放下的信紙,伸手過去,「我看看。」
上面除開寫了甄臨風的的調軍部署,還額外打探來了一個信息——大秦的司金中郎將許睿慈,是蜀國的間諜。
許睿慈是三年前上任司金一職,為人低調剛正,如果張曼蘭不說,根本沒人沒人能想到這樣一個人,竟然藏得這麼深!
司金一職掌管冶鐵、錢幣和農具的製造,也就是說,這三年來,大秦的經濟狀況在蜀國面前完全處於透明狀態。
歷來間諜混入別家朝堂都極為困難,由於這司金一職位的重要性,選擇官員更是極為嚴苛,那就是難上加難,許睿慈能夠成功混上去,簡直可以榮升史上最成功的諜者,不進千機樓當真的可惜了。
不過既然現在這顆釘子暴露了,沈十三隻要把這個消息送回京城就行,皇帝自然會收拾他。
霍清把信紙放下,說,「甄臨風比你還心急,如果你不想喪妻喪子的話,你的夫人,是時候送走了。」
甄臨風新帝上任的三把火燒得極旺,蜀國被他從內到外的整頓了一遍,這還不夠,這次的架勢,看樣子是想借金山一事向大秦發難了。
這個時間段,比沈十三當初計劃的時間還提前了半年。
到時候亂起來,江柔對沈十三來說已經不是一個暖床女了,為了確保她的安全,肯定是要被送走的,不可能把像以前一樣帶她入軍營裡面隨軍。
沈十三說:「再等個把月。」
女子懷胎的前三月極為重要,雖然鄭立人和祝奕說她這胎極穩,但畢竟還沒過三個月,車馬勞頓必然不妥。
現在的情況應該還能僵持一段時間,不會這麼快就起衝突,個把月的時間,等她的胎穩當一些,還等得起。對方這麼痛快就同意了,霍清還頗有些意外,他這次來主要就是跟沈十三說這件事,既然如此,他也就不再多留了。
近些時候,江柔的睡眠質量變好了,不想以前那樣輕輕一點動靜就驚醒,沈十三出去一趟又回來,她也沒有醒。
直到淩晨,已經快天亮的時候,沈十三睜眼就看到她面色痛苦,五官都扭成一團,他立馬起來,要去叫大夫。
江柔拉住他,有些艱難的說,「別去,我腿抽筋了,等會兒就好。」
沈十三掀了被子把她的腿握在手裡一看,確實是抽筋了。
一條硬直的筋從後腿彎開始,把小腿肌肉綳得僵直,他摸索到她膝蓋後窩處兩邊硬而凸起的肌肉,開始大力按壓,江柔神色巨變,強忍了一會兒,小腿上綳直的筋才驟然鬆了,隻是腿上的肌肉還有些抽搐。
沈十三捏住她的腿又按摩了一會兒,問,「好了沒?」
她點點頭,他便去拿了衣服來穿,邊穿邊說,「下個月我讓人送你和沈度回盛京去,我已經讓皇帝解了府邸的封,回去直接住就行,你要是覺得無聊,就把你爹娘接過來。」
江柔愣了一下,「怎麼突然……是因為西北的金山嗎?」
沈十三說:「嗯。」
話中的意思就很明顯了,要戰亂了,所以要先把她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江柔有些悶悶的。
她知道自己留下來隻會是累贅,並不能幫些什麼忙,反而會讓他分心,而且現在肚子裡還有一個,她自己也不敢去冒險。
如果她能像曼蘭一樣,或許能幫得上些忙吧……
她沒再說話,沈十三穿好衣服,準備走的時候,才發現她的情緒不太對,折回來問她,「怎麼了?」
江柔挪過去摟住他的脖子,臉頰在他有些硬胡茬的下巴上蹭了蹭,說,「會不會很危險……你一定要要早點回來啊……」
問了第一句話,她立馬就覺得自己說的是一句廢話。
刀裡來劍裡去,能不危險嗎?
沈十三把手按上她的後腦勺,『嗯』了一聲。
江柔勉強笑了笑,輕輕在他唇上啾了一下,說,「去吧,別耽擱了。」
沈十三留下一句,『好生休息』就走了,獨留江柔一個人在空無一人的房間裡面呆坐。
戰爭啊……
真是令人深惡痛絕的東西。
沈十三走後沒多久,沈問就來扒門。
他一天精力好得很,眼瞅著沈十三和沈度出了門,就躡手躡腳的來了。
把門輕輕推開一條縫兒,見確實隻有江柔一個人,就放開手腳蹦躂蹦躂來了,熟練的往床上一爬,撅著屁股左腳蹬右腳,再換右腳蹬左腳,兩隻小鞋子的落到地上了。
江柔看見孩子,心裡的陰雲散了些,輕輕拍了拍沈問的屁股,「爹爹才走,你不怕他又回來啦。」
小屁桃撅著嘴哼哼唧唧了兩聲,鑽進她懷裡。
**
而此時,蜀國,皇宮。
甄臨風下了早朝,處理完了一堆奏摺,已經是中午,孫公公湊上來,躬身問道:「陛下,已經中午了,可要用膳?」
甄臨風頓了頓,說,「擺駕安福宮。」
孫公公愣了一下,迅速反應過來,唱道:「擺駕安福宮!」
自新帝登基,半月前填充過一次後宮,入住了三位妃子,九位嬪,以及十三位美人,但是各個宮裡一次都沒有去過。
安福宮是皇後的住處,隻有那裡,皇帝去過幾次,但上一次去的時候,似乎是和皇後大吵了一架,發了好大的脾氣,已經好些日子的都沒有去過了。
孫公公正在猜測皇後什麼時候來哄一哄皇帝,沒想到竟然是皇帝主要先去安福宮。
龍輦晃晃悠悠,到了安福宮,早有人通知張曼蘭接駕,甄臨風一進去,她已經準備好了,隻等著他來。
封了後,宮中自有一套規矩,她不能像以前那樣隨意打扮,隻紮一個馬尾。
常年一片色沒有任何花紋裝飾的衣裳被換了下來,換成了繁複雍容的宮裝,長發被綰成一個端莊的髻,頭上零零總總戴了好些不步搖和髮釵,幾乎要把人的脖子壓斷一樣。
她按照規矩,行了一個大禮,周身的飾品撞擊得叮噹作響,甄臨風靜靜站著,等她行完禮,側頭看了孫公公一眼。
孫公公立即吩咐下去上膳。
甄臨風昨天通宵批奏摺,今天一早就直接上朝,連早膳都沒來得及用,早就餓了。
傳完了膳食,他掃視了一圈一幹宮女太監,說:「退下。」
孫公公立即帶著眾人退下。
甄臨風把張曼蘭晾在一旁站著,自己端了碗,也不要人布菜,自顧自吃了個七八分飽,漱過口,慢悠悠道:「怎麼?還不說?」
張曼蘭斂眉道:「沒做過的事,我是不會承認的。」
言辭篤定,神色間一派坦然。
甄臨風說,「別嘴硬,你是朕的皇後,朕可以饒你一次。」
張曼蘭跟了他多年,深知他的脾性。
他可不是什麼說話算話的君子,對於異心者,隻會一律格殺,所以她當人不能承認,「我沒有。」
甄臨風說:「既然這樣,那我們就等著,如果三個月內許睿慈暴露身死,那就是你,如果不是,便是朕冤枉了你。」
張曼蘭神色平靜,「陛下,是誰跟陛下說我叛了?是蘇月嗎?就算許睿慈死了,憑什麼說是我背叛?許睿慈是誰,我連這個名字都是從陛下口中得知,蘇月比我知道得多,為什麼不是她捏造事實栽贓我?」
甄臨風說:「朕隻相信證據。」
張曼蘭說:「那陛下將證據拿過來,將造謠我背叛的人喚來,我們對峙。」
甄臨風當然沒有證據。
張曼蘭自己做事,自己知道,她手腳利落,沒有目擊證人,也不會有證據。
甄臨風留她這麼久,正是沒有證據,否者他上一次來問罪的時候,她就已經死了。
可是他生性多疑,雖然沒有證據,但有人在他心中種下了懷疑的種子,他也不會再全信張曼蘭了。
甄臨風卻全然不聽,說:「三個月,朕再等三個月,這三個月,你就禁足在安福宮。」
他沒有說如果許睿慈沒死會怎麼樣,死了又怎麼樣,但是張曼蘭知道,許睿慈死了,她也必須死。
不管到底是不是她做的。
甄臨風就是這樣一個人,他不相信任何人,也不會留任何隱患在身邊。
雖然她並不冤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