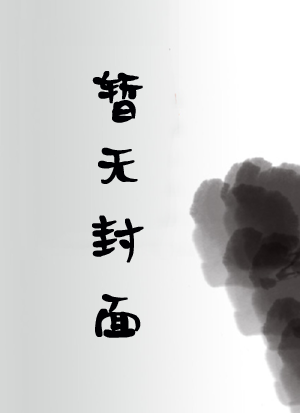就在左丘吾踏出意海冰棺的那一刻——
冰棺之上,菩提樹動。
黃弗擡起頭來,手上的降魔杵,似佛塔倒豎,紮在了黃舍利身邊,予她以悟道的保護。老農般的粗粝五指隻是那麼一抓,便将身上的破裘衣,扯作了舊袈裟。
當年風雷廟裡破戒的小和尚,已經修成正果,可是那個為他縫袈裟的左道妖女,卻已經不在了。
他搖身而起,這袈裟便系成了戰袍,黑褐的皺臉上,似塗了金中帶皿的漆,化成一尊兇威滔天的……“佛”!
佛陀的慈悲,堆在生皺的眼角,似滅世的狂笑。
他當然不是真正的超脫覺悟者,距離不朽還遠得很,但在北域兩大霸國的托舉下,也算是真正地凝聚了佛身——
有一道身影更比他快。
在他把袈裟展成戰袍的時候,青衫挂劍的姜鎮河,已在高天上。
天無痕,海無波,沒有什麼喧嚣的光華,卻有告死之鳥的陰影,在他身周繞飛——
壽逝魂消,道則凍結,于是這風平浪靜的意海中,便恰恰地浮現了一縷“不協”。
禮恒之的身影,就從那沖突于此境的“不協調”中走出。
就是為了這場審問不受外力幹擾,太虛閣衆人才大費周折,将左丘吾分鎮。且由姜望親鎮左丘吾真身。
可禮恒之竟然在不知不覺間,找到了這裡!
儒宗二老雖然并稱,看起來這“禮老”強過“孝老”不止一籌。
但他不請自來,所要面對的,不止是瞬間将他逼出形迹的姜望,不止是顯化佛身的黃弗,還有那冰棺之上,如山巒倒伏,卻又驟止雷霆鼾聲,拔身而起的卞城閻君!
更有一輪明月,悄然懸照在海。
還有一縷無處不在的劍光,逐他而來,先他而至,懸指他的眉心。
禮恒之到底是顯學宗老,面對這些,仍然不見波瀾。隻先一步開口:“我不是你們的敵人,書山也不在太虛閣的對立面。”
“太虛閣沒有與任何人為敵的計劃。”姜望不動聲色地站在他面前:“……但受到威脅的時候,也不介意被誰視作敵人。”
禮恒之本來是想看看左丘吾的情況,然後再決定要不要把這位院長救出來,但沒想到他好不容易找來,左丘吾卻已經先一步離開。
留在這裡已經沒有任何意義,他斟酌着措辭:“我特地找過來,隻是想問一句——鎮河真君放左丘吾的真身出去,是否代表太虛閣的立場?”
姜望隻道:“我也沒有阻止司馬衡。”
“劇匮沒有在法理上看到錯誤,黃舍利沒有在時間上看到謊言。左丘吾和司馬衡各有其道,他們之間究竟孰是孰非,太虛閣無法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來評判。理想的錯謬與正确,何能輕易言之!”
“左院長向我承諾了鐘玄胤的安全,也向我承諾了交代——”
他平靜地道:“我姑且相信,謹慎觀望,等待真相。僅此而已。”
“既如此,那就再看看。”禮恒之說着便要轉身離去。
“留步——”姜望很客氣:“既然來了,先生不妨就在這裡看。”
禮恒之擡眼看他:“這隻是我的禮身。”
姜望面無表情:“都一樣。”
……
……
那些“都一樣”的曆史,都已經翻篇了!
此間棋格囚籠,書簡也貼着牆。勤苦書院寫成了史書,古往今來的力量,都彙聚一時。
左丘吾把聖魔按在了牆上,極其粗暴地往書簡上撞。書簡、鐵壁,兩層夾牆,哐當哐當的響!
已經在不同的曆史篇章裡被削弱了很多次,又被鬥昭殺得僅剩頭顱的聖魔,哪怕再次吞食其潛于書院曆史的魔意,也根本不是左丘吾的對手。
吞食魔意,隻是魔功不願意消亡的本能。
左丘吾一個照面就将其打得瀕臨崩潰,正是利用這種本能,滌盡勤苦書院曆史中的魔性殘毒。
他以五指覆其面目,似乎根本不願看到那張臉。
就這樣一次次地按砸,冷酷而兇暴。
哐當!哐當!哐當!
聖魔顯化的肢體,無力地垂在牆上,聖魔的魔顱被撞塌了!
被撞碎的魔氣染在青簡上,留下了詭異的花紋。
左丘吾卻在這樣激烈的時候,擡起另外一隻手,往上方一抓——
在棋盤上間隔頗遠,探進那個丢失了黑子的棋格裡,探進其所束之的“高閣”。衆隻見虛空隐隐,圖影模糊,這隻手似乎抓住那卷封印了黑棋的書簡。
他扯住了一團嘶叫着的什麼,從那高閣拽落下來!
左丘吾此刻的狀态幾近癫狂,完全不見平時的宗師風度。
可心裡卻是靜海一般。隻在漣漪微起的時候,有微不可察的心聲:“等你的學生成道……你再回來吧!”
哪怕儒聖蘇醒,抑或【子先生】走出那一步,也都不能保證司馬衡的性命,不能保證他直筆不悔的道。
儒祖難道就很願意聊一聊當初毋漢公的死?
【子先生】這麼多年神神秘秘,難道願意面對天下剖白他的一生?
這還隻是儒家内部!遑論放眼于外。
司馬衡名傳天下,天下敬他者衆,恨他者也衆!
左丘吾右手按砸的聖魔,已經不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。
所有人都看着他左手拽下來的那團扭曲虛影——憑借整部《勤苦書院》所加持的力量,從曆史窗口的投影中,從迷惘篇章裡,從司馬衡的身上拽下來!
在司馬衡被逐回迷惘篇章而不能自主行棋的時刻,代他落子,拔下他的毒瘡。
那是一團不斷嘶叫着的文字,那是一個在墜落《勤苦書院》的過程裡,不斷清晰的人影。
當這個人影穿越了【黑白法界】,落進棋盤中,五官已經明确。
此人的面目,令姜望都是一驚!
顧不得再盯住禮恒之的禮身,冰棺頃刻碎滅,禮身亦被逐出。湖心亭裡的衆生僧人,一霎化歸為姜望本尊,手按劍柄,傾身瞰棋盤。
亭外風雲動!
隐隐有一座無上仙宮,缥缈在虛無之中。嘩嘩嘩嘩的翻書聲,隐約曆史在向仙朝倒伏——
勤苦書院的曆史有無窮的演化,理論上也可以走向仙人時代。畢竟許懷璋當年也是儒家禮師,這條道路是貫通的。
被左丘吾拽進棋閣裡的人,五官俊美,氣質不凡,分明是七恨魔主的樣貌!
或者應該說是“吳齋雪”。
此人并非後來的成魔姿态,倒像是過去曆史中的吳齋雪。
這時候的吳齋雪,還身穿白衣,是翩翩書生。
但越是強者,過去越是不可改變。要想在“過去”殺掉某一個強者,所要付出的代價,往往超過現在。
超脫之路,更是一證永證。吳齋雪已經以七恨之名超脫,在過去、現在、未來,都是不朽的存在。怎麼還會出現這樣一具被死死壓制的顯身?
這一刻的吳齋雪,更像是吳齋雪的曆史投影。是在某個時刻,以吳齋雪的曆史姿态所留下的剪影,屬于照貓畫虎,而不是真正的惡虎。并不是真正從某個時空抓來的吳齋雪。
左丘吾當然知道他把吳齋雪拽下來,是一件多麼令人驚懼的事情。他也已經感覺到,一道道恐怖的攻勢已經臨身待發。一旦他的解釋不夠合理,剛才選擇了中立的太虛閣,立刻就會與他對決生死。
他說道:“當年的《禮崩樂壞聖魔功》,本是以吳齋雪為目标!”
“苦于天人永淪之厄的吳齋雪,卷進帝魔君的布局裡,本該成為聖魔君歸位。”
“那是一段漫長的故事,總之吳齋雪一步步走到了絕境。”
無一錯一首一發一内一容一在一一看!
“避無可避的他,卻回馬一槍,彰顯極欲,不棄禮樂,主動選擇了《苦海永淪欲魔功》!其以欲魔君之尊降臨魔界,算是撬到了一點主動權……此後又以《七恨魔功》替之。”
“那時候的吳齋雪,是遊曆天涯的史家名儒,其出身的南山書院,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被夷平。他跟我們勤苦書院的一位大儒交好,那時常來書院讨論學問——”
“選擇《苦海永淪欲魔功》的時候,吳齋雪也把這部攤在他身上的《禮崩樂壞聖魔功》,隐秘地留在了書院裡,等待這部魔功獲得傳承。”
“這就是勤苦書院留存此功的原因。”
“在樓約成就恨魔君、田安平成就仙魔君後,想必諸位也不難看出來,這部《禮崩樂壞聖魔功》的伏筆,就是七恨為自己超脫這一天所做的安排。”
左丘吾五指成籠,将閉着眼睛的吳齋雪囚于其間。
另一隻手仍然按着聖魔的頭顱在撞,如舂米搗蒜。
在接連不斷的哐當聲響裡,他繼續說道:“司馬衡早就察覺到不對。但因為被魔意所侵的幾位書院高層的阻撓,他當時沒能揪出《禮崩樂壞聖魔功》。不過他也在曆史長河裡截取了吳齋雪的投影,存留在時間墳場,等待有一天将其反制。”
“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,七恨會跳出魔祖所定的命運,成就超脫。也沒人能想到,司馬衡會失陷在曆史裡……”
“七恨成就超脫後,祂的一切隐患都被抹掉,一切分離都要回歸。但因為【曆史墳場】和【迷惘篇章】的特殊性,這份投影沒有立即回去,也無法體現超脫的力量。”
“可因為超脫者的強大與不可測,這份名為吳齋雪的投影,還是侵染了司馬衡。”
“這是司馬衡迷惘的原因,這是劇真君你覺得他有時候不是他的原因。”
左丘吾認真地道:“他有時候的确不是他,他有可能作為史家宗師吳齋雪歸來。”
這的确駭人聽聞。
意海之中,白日夢橋上,衆人不免各驚。
但在湖心亭裡,也都沒有表現。一個比一個鎮定。
“所以,這才是左院長一定要封印司馬衡,将他束之高閣的原因嗎?”秦至臻沉聲問。
當左丘吾将整部《勤苦書院》的力量都調動,棋盤的部分限制已經被打破,内外交流不必再通過棋子。
衆人瞰棋格,如立井邊觀井中。
左丘吾在井中搖了搖頭,否決了秦至臻善意的猜想。
他說道:“我把司馬衡推回迷惘篇章的時候,還不知道他被吳齋雪侵染了,這是最近的對弈裡,他用他的棋告訴我的。”
“左先生現在要如何作為?”劇匮淡聲問。
左丘吾定聲道:“我封禁司馬衡,跟吳齋雪無關,是因為他走錯了路,還執迷不悟。我用《勤苦書院》全部的力量,剝下吳齋雪,也跟司馬衡無關,是要吳齋雪償他的債!”
他說得非常硬氣,但要讓吳齋雪償債,談何容易!其已是永證的超脫者。
但左丘吾卻心有成竹。
他拽着手上這個名為吳齋雪的投影,一把砸進了已經看不出樣子的聖魔殘顱裡,砸出無數禮義仁孝代表秩序的文字,厲喝道:“聖魔君!今有歸!”
聖魔君歸位,的确大益于魔族。
但聖魔君在今天這個時間點,在這間棋格囚籠裡歸位,卻是注定了結局。
可以登頂魔界的聖魔君,在這裡根本無法強勢。
更沒有什麼存在,可以把這尊聖魔君迎回魔界。
哪怕是七恨!
鬥昭一時恍然:“原來如此!煉化具有不朽之性的《禮崩樂壞聖魔功》很難,但殺死聖魔君卻很容易。你是為了用聖魔君來消耗聖魔功,推遲聖魔君歸位的時間——一旦殺死聖魔君,魔功又要解而重化,至少在神霄戰争之前,無法再聚攏,也就不影響大局,可以往後慢慢處理!”
但他又皺眉:“不對……”
靜瞰棋盤的姜望已經開口:“如何能輕視七恨呢?既然吳齋雪已經侵染司馬衡先生,說明您和司馬衡的這局棋已經被注視,超脫者的目光落下來,你所有的謀劃都會被影響——不,都已經被影響了。怎麼還敢按部就班?”
對于七恨的恐怖,這世上恐怕沒有幾個人,能比姜望認知得更深刻。因為他已經視此不朽存在為人生大敵,和重玄勝研究了很久。
他現在都能背出吳齋雪的生辰八字,把吳齋雪所能找出來的曆史議論都倒背如流!
“姜真君說得沒錯。”左丘吾道:“當吳齋雪睜眼,成就聖魔君。七恨必然會有反應。”
“在祂的注視下,我所有的落子都是不确定的。”
“但有一點,在吳齋雪成就聖魔君的時候,就已經不可改變。”
天下第一書院的院長,有幾分恩仇得解的快意:“魔君歸位,存在于魔祖歸來的命運!祂以七恨之名,跳出了魔祖安排的命運。可是又以吳齋雪之名,跳進魔祖安排的命運裡。”
“在所有針對七恨的結果裡。這是最傷害祂的那一種。因為這關系到了祂的超脫根本,也必将動搖祂在魔族的所有布局!”